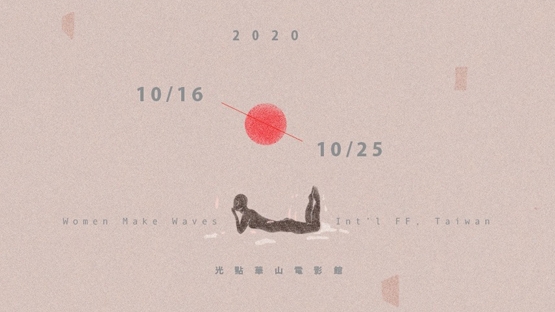木蘭選片 《孟加拉製造》馬欣:為何女人的面具總是場集體共業?
by 馬欣
《孟加拉製造》不僅是部描寫女性處境的電影,更為今日這世界的階級做了一縮影故事,龐然的勢力與螻蟻的求存,讓電影中的故事不限於哪一個國家。
電影一開始,讓觀眾感受到的就是成衣加工廠裡密麻的座位,電扇無力地吹著熱風,你可以感受到那僅容轉身的通道,與女工們趕製衣服時沒有停過的手腳動作。你甚至可以嗅聞得到那空中翻飛的棉絮,無論是氣味、溫度,那裏都不適合人久待的,也都標明了那裏是個嚴苛的「勞動場」。
然後那裏一場火災,女工匆忙逃竄,原本高溫的室內一陣煙霧,顯示著沒有安全配套的工作單位。那裡的女工們都很年輕,雖然許多已嫁做人婦,但還看得出屬於女孩的稚嫩,身上穿著嫩綠粉彩,像是在那鐵鏽斑斑的地方,一點青春仍還殘存其中,但那點青春卻與他們的勞動動物般的人生是如此違和。
導演捕抓著她們還有點懵懂的青春與笑語,讓那嚴酷的加工速度中,仍有一抹生氣的剪影,同時你很快地感受到這部電影拍出了漢娜鄂蘭所寫《人的條件》裡,所謂「勞動的動物」。這其中也包含了在台灣的我們。
因為電影《孟加拉製造》裡,隨著平價成衣業的興起,女工們一天處理成千上百件服飾,論件數更為嚴苛與快速,而同樣身為「勞動的動物」的我們,為何那麼需要消費生活的過剩品;需要報復型消費來紓壓,這些都是因為我們正是同屬於「勞動動物」中的一環。在後資本主義成為權力的魔術箱後,我們與她們既遙遠又靠近地出現連動效應。
只是我們如今的過剩品需求,也改寫了孟加拉女孩們的生活方式,因此電影中有一幕特寫在照女工腳踩在縫紉機下方的頻率,如同老鼠滾滾輪,也如同犁牛耕田一般不得停,我們都屬於體制之惡中,也成為羅網上的蝴蝶掙扎著一點生氣。

而這部電影更反映在後資本主義時代女性的處境,一如印尼外勞大量輸出後,印尼的邊緣城市常見的是年輕女性都出外工作了,男性則負責帶小孩或長期失業在家。這部電影裡的女性也與印尼女性處境一樣,必須撐起代工與世界經濟變遷的壓力,馬不停蹄地換取低廉薪水,但一件T恤在國外的售價是她們做上幾百件都還買不起的,她們買不起她們做的衣服,如同台劇《做工的人》中所說的:「我們蓋的房子都不是我們買得起的。」
後資本主義成了金權遊戲的工具。《孟加拉製造》很忠實地拍出了冰山的一角。而現代女性往往在這樣的金錢遊戲中,成為相對被壓榨的一群。女主角希姆必須兼顧家內外的事情,並要顧及失業丈夫的自尊,但沒結婚的女同事則更恐慌成為社會中被歧視的弱勢,讓人想起韓片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那母女有苦說不出的狀態,要兼顧所有的角色,輪到她想為自己發言時已經說不出來。而希姆也是,當她發現被老闆苛刻薪資,且違反勞工法時,想要站出來,卻在其他女工眼中被視為「害群之馬」。
女生躲藏在受人指教,與受人歡迎的面具下太久也太習慣,一旦想拿下面具時,發現第一個不習慣的有可能竟是同性,像我們的面具是一種集體共業,也是一種集體的默契似的。女性常被視為群體性的,無論在職場上還是在社會的角色功能上,一旦有了希姆這樣有所自覺的,就受制於受害者結構中的狼羊一家的牽制,這也是多年來,男性雖然在經濟上備受壓力,但整體的世界仍受父權的遊戲規則所控制。

其中深刻的是,有一女權與勞工運動者鼓勵希姆站出來,提交罷工申請與主管談判,但那名女權主義者明顯是生活優渥者,她不能理解希姆的腹背受敵,階級如同密室,她那以上望下的姿態,也無形中成了共犯結構的一環。
當今,有些男性聽到女生講父權結構就會反彈,但其實這並非是指個人,而是經濟本質成為金權遊戲後,男女都是被控制的勞動動物。這部電影裡,希姆的丈夫的矛盾與懊惱何嘗不寫實?因此它不只是部女性電影,而是從各個視角來看21世紀女性的處境,孟加拉離我們並不那麼遠,當經濟的暮色已深時,這部電影有它可觀之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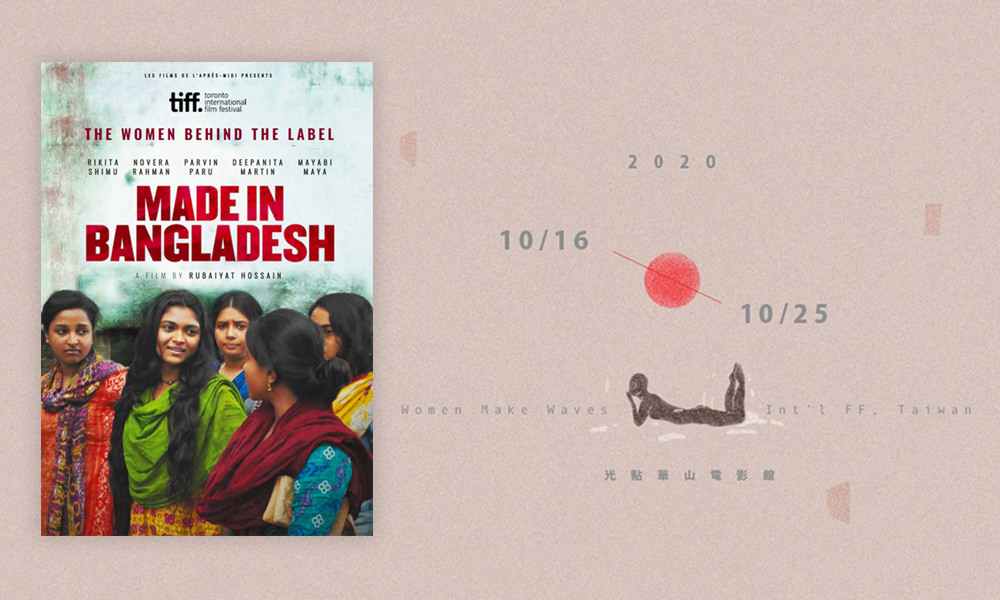
同場加映
購票資訊詳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