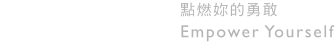木蘭書房 極地暖化下的森林哀歌:北方、毛樺與消失的馴鹿路線

「當氣溫升高,人類能輕易開啟空調享受舒適,但森林無處可逃。它們只能緩慢向北推移,在乾旱與土壤變遷中掙扎求存。」——林子平
森林的先驅者:毛樺站在北方變遷的門口
往市中心的道路兩旁是一排排年輕的歐洲赤松,橙色的樹皮和新雪形成對比,其中攙雜了較矮小、顯得破破爛爛的毛樺,樹幹凹凸不平,樹枝乾癟,以及有如扭曲手指般的細枝。我正是為了這些樹而來到這裡,在隆冬的週一早上九點造訪哈爾蓋.史崔菲爾德的辦公室。史崔菲爾德是阿爾塔市計畫部的部長。
毛樺是北極少數的幾種闊葉落葉樹,比大部分的針葉樹還要耐寒。毛樺的「毛」,是指一層柔軟的絨毛,能在嚴寒中發揮類似毛皮的作用。在較低的緯度與海拔,毛樺常和松樹與雲杉共生;然而過了某些海拔與緯度的界線之後,樺樹便會拋下其他樹木,獨自繼續往北數百哩。

這種堅韌的小樹樹枝粗短,樹皮坑坑疤疤,看上去不怎麼討喜,甚至可說是難看,但卻是北極地區的倖存者,亦是先驅,對北極的人、動物、植物都至關重要。人類用毛樺製作工具,建造房子,做成燃料、食物與藥物,而毛樺上則長了食物鏈裡關鍵的微生物、真菌和昆蟲,也為組成森林所需的其他植物提供遮蔽。
少了樺樹扮演的先驅角色,北方生態系會演變成不同的模樣。毛樺決定了其占據之處的哪些生物能生長、存活、移動。隨著北極升溫,那個範圍迅速擴增。在歐洲遠北暖化中的生態系裡,設定計畫的除了人類,就是毛樺。
哈爾蓋說:「沒有雪的時候,一切都會變得更加黑暗。小時候,爸媽總說我們十月十日就得為冬天做好準備。」而近年的冬天逐漸變暖,他說,二○一八年的十一、二月尤其暖得「誇張」。整個社群都陷入恐慌中,馴鹿牧人在臉書上貼了凍原無雪的照片。

哈爾蓋是都市人,戴著一副無框眼鏡,看上去個性溫和,氣質內斂。他有一半的薩米(Sámi)血統。薩米人是歐洲極地的原住民,和環極圈民族有共同的DNA和語言傳承。
薩米人曾經不受阻礙地在大地遷徙,但如今剩餘的八萬人卻發覺自己成了四個現代國家——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俄國——的公民。薩米人是唯一被聯合國承認的歐洲原住民團體。
鹿群的步伐,是馴鹿牧人的方向

打自馴鹿神灑下馴鹿血形成河流,用馴鹿毛皮在地上播種形成草木,並且把馴鹿的眼睛拋進夜空,變成一萬年前的星辰以來,薩米人就活在其他歐洲人口中的「拉普蘭地區」(Lapland),以及他們自已口中的Sápmi(薩米人的土地)。他們的岩石藝術描繪著數千年來一貫的生活方式。碳定年到八千年前的圖畫顯示,火柴人乘船捕魚、獵熊與駝鹿、放牧馴鹿。
馴鹿是哈爾蓋認同的中心,也是所有薩米人認同的中心。哈爾蓋的母族是馴鹿牧人,哈爾蓋既屬於城市,也屬於帳篷。在一個薩米人的文化活動,他身穿繡金的傳統薩米毛氈外套、絲質圍巾、馴鹿皮褲和皮靴,以及精巧的錘紋銀腰帶。他是理性國家的代理人,官僚與混凝土的供應商,但也流著游牧民族有翼的血,渴望不被人統治,只受馴鹿群的需求驅策。

每隻馴鹿都有個薩米名字,牧人認得自己馴鹿群的所有成員,甚至僅靠觸摸也摸得出差異。「愛」這個字已不足以描述這樣的關係,「共同依存」或許更為貼切。馴鹿讓薩米人在酷寒與冰雪的無情世界裡活下來;不論是誰,只要身上沒馴鹿毛皮做的衣物或鞋子,在那個世界絕對活不了。人們遷移,是配合著馴鹿覓食吃草的腳步而移動。他們的整個文化都是圍繞著馴鹿群的遷徙需求而演進。
樺樹是牧人的附屬品。從遮風避雨到燃料到運輸,要在這裡生活,樺樹就不可或缺。樺木能作為支撐帳篷的支架,也可以製作滑雪板、雪橇,讓人們從海邊茂盛豐美的夏季牧場遷移到冬天高原上的苔原。不過,氣候崩壞打亂了這個循環,薩米人成為氣候變遷的第一批受害者,被迫比我們其他人提早思考整個文化崩壞的事。
文化如雪,暖化讓薩米文化無聲流失

薩米人曾經有過更多樣的文明,包括住在樹木中的森林薩米人,以及住在海岸的打魚薩米人,然而,馴鹿是其中碩果僅存的台柱。森林薩米人住在草皮屋裡,不屑像挪威人那麼浪費,用木材建造住家——木材應該只用來做成工具和船、當作燃料才對。但他們早已不在了,一個世紀多之前被挪威政府強迫選擇畜牧馴鹿或同化。飼養動物取得肉類是政府認可的事,而在森林裡自給自足卻無法符合政府的經濟目的與效益。
捕魚的薩米人花了更多時間整合,然而,最終是數量大減的鱈魚促使他們加速搬去城裡,而負責管理這個過程的人正是哈爾蓋。阿爾塔這座城市欣欣向榮,居民有五萬人,但阿爾塔成長的同時,周邊的郊區人口卻在逐漸流失。
挪威其他地方重視放牧馴鹿,因此方法被保留了下來。薩米人總是把肉賣給南方人,馴鹿肉是昂貴的珍饈,很久以前就成為挪威文化的一部分。挪威政府把馴鹿視為豢養的資源,有配額、補助,以及嚴格的數量控制。
在官方眼中,馴鹿是商品,北方廣大的高原缺乏其他生產力,而馴鹿是有用的出口物。但對薩米人而言,馴鹿不只有經濟和文化意義,也是象徵。哈爾蓋的皮褲印證了這一點。
他說:「馴鹿是生命,馴鹿是一切。沒有了馴鹿,我們終將不存。」
放牧馴鹿曾是薩米人萬年不變的生活方式,如今面臨了威脅。暖冬會要了馴鹿的命。
攝氏零度下的崩塌:北極冬季的脆弱進行式

從前,冬天的初雪大約在十月落下,最初是在凍原、森林線上的高原,然後是河谷與海岸的松樹和樺樹林。不久之後,溫度計的水銀會降到冰點之下,並持續到四、五月,屆時冰雪開始融化,河水會湧動著高含氧的碎冰而呈現清澈的藍綠色。
二○○五年以前,冬季平均氣溫是攝氏負十五度,且至少會有一次穩定降至負四十度,鏟除最耐寒的昆蟲幼蟲;這個過程會保證北極的夏天潔淨無蟲害。這樣的冬季世界黑暗、寒冷而乾燥,在那樣的溫度下,空氣裡幾乎沒有濕氣,雪堆有如均質的砂,由幾層大顆的雪結晶(seaŋáš)組成。當溫度在隆冬時刻來到攝氏負四、五十度時,雪結晶的品質和性質,對人類與動物的存活至關緊要。
大顆雪結晶對密度均衡的健康雪堆(guohtun)不可或缺。大顆雪結晶讓馴鹿能用鹿角、蹄和吻部撥開雪,找到星石蕊(Cladonia stellaris)——這種長在地上的地衣富含碳水化合物和糖,通常與凍原上的草共生,是適合冬季快速移動時補充的高能量食物。凍原沒有樹,所以當風橫掃高原時,會把細粉狀的雪吹成一層淺淺的保護毯,覆蓋、保存雪下的地衣。

不過,當溫度回升至零度,甚至高於零度的時候,這個脆弱的冬季生態系就會崩潰,即使只是少量的升溫也可能釀成大禍。
雪堆在攝氏負五、六度會開始出現水分,失去砂子般的特性與質地,大顆雪結晶融化,雪堆開始被馴鹿的蹄子踩實,破壞下方的草料。如果溫度一路升到零度以上(近年愈來愈常這樣),就會成為大災難。當溫度再度掉到零下時,融雪或雨水會結凍,在地面上形成一層冰殼,封鎖植物,阻止馴鹿覓食。
二○一三年曾發生過這樣的事,之後二○一七年再度發生。數以萬計的馴鹿死亡,有些牧人失去超過三分之一的牲口。過去一百三十年來,冬天的溫度曾有三次爬到零度以上,而僅僅是過去十年就發生兩次。
預估從現在起,每年冬天都會出現溫度超過零度的日子,這也意味著,植物被鎖起來的日子將無可避免。如果濕度太高導致地面凍住或食物供應不足,母馴鹿甚至會刻意讓未出生的幼崽流產;其他幾種哺乳類也有這樣的行為,例如小鼠、猴子和虎鯨。
暖冬意味著馴鹿群需要更多的空間覓食,只是牠們在凍原還得面對來自風電場、高壓電塔、道路、礦場和其他馴鹿的共同競爭,而且情形益發嚴峻。
摘文節錄自:《尋找北極森林線:融化的冰河、凍土與地球最後的森林》
出版:行路
作者簡介:班.勞倫斯(Ben Rawlence)
著有《剛果電台》(Radio Congo: Signals of Hope from Africa’s Deadliest War)和《荊棘之城》(City of Thorns: Nine Lives in the World’s Largest Refugee Camp),曾為《衛報》、《倫敦書評》(London Review of Books)、《紐約時報》、《紐約時報書評》、《紐約客》雜誌和其他許多出版物撰寫文章。現居威爾斯,是黑山學院(Black Mountains College)的創辦人兼校長,這間機構致力於幫人們對不久後的變動做好準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