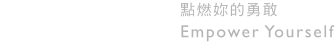女人沙發 劉安婷與陳慧潔 打破規則夢更大
by 李玉玲讓自己「破碎」,生命最深刻的價值才能被活出來。
「女人沙發Women’s Talk」來了兩位最年輕的與談人,二十五歲的劉安婷和十七歲的陳慧潔。 與其說女人的對談,女孩的聚會更貼切。碰面那天,陳慧潔雖因中暑發燒,依舊充滿朝氣,對談結束還拉著安婷姐姐玩自拍。
談起正事,女孩不見了,而是有想法、有願景的成熟年輕人。劉安婷,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大學畢業,放棄在美發展機會,回台創立非營利組織「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」,推動偏鄉教育;陳慧潔,小二起在家自學,八歲跟著牧師父親為獨居老人送餐,投入社會公益,十四歲起應邀到各大學演講。一位是體制內資優生,一位是自學的傑出青少年,成長的路儘管不同,都走出一條陽光大道,這條路不是父母學校幫她們選好,而是自己選擇,並為自己負責。
問:談談不同教育背景對成長的影響。
劉安婷(簡稱「婷」):我好勝心很強,覺得自己的價值要透過比別人厲害來證明,念小學開始不管比賽或考試,一定有我,從總統獎拿到台中市長獎,是學校風雲人物。一次小考考了第二名,我生氣大哭:怎麼可以考第二!爸媽擔心我的世界變得很狹隘,反而要我別只在意成績。

問:父母灌輸妳們什麼樣的金錢觀?
潔:父母教育我們獨立,包括金錢的自主管理,我家四姐妹從小拿零用錢長大,底薪十元起跳,隨著年紀逐年增加,洗碗、曬衣服、每天準時靈修……再加一元。
我三歲學切菜,五歲洗碗,後來媽媽告訴我:其實我都沒洗乾淨,但她不會因此不讓我做家事,而是等我睡覺後再把碗重洗一遍。過年收紅包,錢被爸媽拿走,只留下紅包袋,我聯合姐妹們「抗議」,經過家庭會議討論出處理原則,以後不管是紅包或演講費,任何收入,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,十分之三繳庫給家裡,十分之三是教育基金,十分之三零用錢。
現在我負責一個非營利組織,更要學習如何管理才能使組織健康運作。歐美的非營利組織都是提前一年募足經費,確保存款水位安全,避免臨時無法處理的風險。
問:父母對妳們的影響?有叛逆期嗎?
婷:母親很懂得放手,她帶我學鋼琴、跳舞,但從不逼我,小時候上過兒童英語班,沒太大興趣,到了國中想讀《哈利波特》,有了強烈的動機,英文進步非常快。
爸爸是傳統父親,努力工作養家,但給我很大的支持,國中參加辯論比賽前,他會陪著我練習,我要去美國讀大學,他也鼓勵我:「神會給妳最好的。」父母不會把他們的期待套在我身上,要我對自己的選擇負責。
母親在我升國小六年級時罹患癌症,看到她剃光頭接受治療,受衝擊很大。母親生病,升上國中又因為自大受到同學排擠,青春期的我想要長大,又被當成孩子看,心裡從不知所措變成莫名的憤怒,好像全世界都對不起我。幸好,父母耐心等我開竅,後來有了信仰,我看到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全能,開始重新定位自己。
潔:爸媽訓練我們從小獨立,我十一歲到台北治療假性近視,媽媽帶我坐一次車,以後就讓我自己來;十四歲開始演講也是一個人全台跑,他們的確很勇敢,讓我做各種嘗試,除非我問,他們不會說自己的意見。哈!就算講了,通常我也不採用。

問:安婷高中暑假到史丹佛大學念夏季學校,那次學習對妳有什麼衝擊?
婷:那個課程主要是為美國高中生設計,我是格外稀少的外國學生,一個人被丟到陌生的環境,看到的不是「觀光」的美國,而是完全不同的教育體制,考試時一張空白紙,題目寫在黑板上,我問老師:要我畫表格嗎?條列式嗎?什麼規格都沒有。
台灣的教育都幫你做好選擇,連讀大學也由分數決定,遲至十六歲我才意識到:最高深的知識往往沒有標準答案,頭腦更高的價值不是背誦,而是思考。美國學生敢於探索,敢於犯錯,夏季學校課程結束回台,我非常痛苦,為什麼我的選擇只有一套公式,高二升高三時決定出國念大學。
問:慧潔曾說除非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,否則不會上大學,妳對體制內教育有何觀察?
潔:我問同輩的人夢想是什麼?十個有七個講得出來,但問何時實踐?大部分都說:考上大學再說。我問大學生的夢想是什麼?十個有七個回答:不知道。這與台灣的教育制度有關,考試最多的是選擇題是非題,從小到大都有標準答案,沒人問我們的想法,到了大學突然問,當然不知道要做什麼。
前陣子去清華大學旁聽兩周的課,蠻新鮮的經驗,我對管理有興趣,大學還是有可學的知識,但我不會為了畢業證書跑去念大學,還有一年多可以考慮,我不急也不擔心,看上帝如何帶領。
問:安婷到普林斯頓大學念書,開啟什麼樣的視野?
婷:兩百多年歷史的普林斯頓大學像一座金庫,資源機會放在那裡,將學習主權交給學生。第一次去非洲迦納,不是為了當志工,而是修社會企業的課程,每天上課只有一兩小時,剩下的時間就去做志工,當助理導師。後來又去法國、海地、日內瓦等非營利組織實習。如果沒有這些機會,現在的我會貧乏許多,我在普林斯頓學到的不只是課堂上的知識,而是主動問自己到底要什麼?不害怕敲門,這扇門沒開就再去敲下一扇門。
問:大學畢業後原本有不錯的工作,為何回台創立「為台灣而教」?
婷:台灣學生在「全世界學生能力評比」(PISA)表現優秀,數學能力更是排行前五名,但低成就學生比例也高於其他國家,最好及最差的學生差距竟然達到七年,說明台灣教育出現嚴重的資源分配問題。越弱勢的學童越需要優秀的老師,台灣的現況卻剛好相反。

原以為要年輕人去偏鄉蹲點很困難,「為台灣而教」第一年只開了八個教師名額,沒想到收到近兩百份申請書,今年增加為二十名,報名人數也增加到三百多人。年輕人願意成為改變的一份子,把大於自己的願景扛在身上,有太多深刻的故事,偏鄉的教育困境正在改變。
問:慧潔對於社會服務有什麼新的想法?或者想要探索其他領域?
潔:社會企業的確是讓非營利組織永續經營的方式,但我是目標導向的人,不會為了做而做,必須看見需要,才有強烈的動機去完成。去年,我去台中幫一位教會師母競選市議員,原本覺得政治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,但實際參與後想法改變了,政治與我們息息相關,它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,也可能變得更壞。雖然師母沒選上,但那半年我看到政治的影響力,今年,宜蘭縣政府邀我加入青年事務委員會,沒多考慮就同意了,開縣政會議時可以提案建言,很酷的工作。

問:兩位年紀輕輕就受到社會關注,如何維持謙卑的心?
婷:能夠做好一件事受到社會注意,絕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成,記得初衷,不要讓成就變成堵住耳朵的東西。
電影《納尼亞傳奇》森林之王獅子要拯救被壞女巫抓走的孩子,原本,殺死女巫對獅子來說輕而易舉,牠卻選擇把生命獻出去。或許讓自己「破碎」,生命最深刻的價值才能被活出來。我感謝生命中有像獅子一樣的榜樣,讓我看到人的價值不是以數字或地位來定義,走出舒適圈或許會破碎,但帶出的影響力也超乎想像。

我工作和生活分得很開,雖然不致於不顧情面,但工作時必須「沒大沒小」,忘記年齡,否則什麼都做不來。我喜歡甘地的一句話:「成為這世界你想要看見的改變。」可以透過自己的故事影響別人是一件很棒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