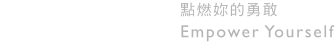女生去流浪 給山迪
by 鄭欣娓我好像慢慢開始了解這是這麼一回事,又好像愈弄愈糊塗了。我們曾經怪罪種姓讓我倆無法自由地相愛,但我在印度的這幾個月裡聽到愈多故事,就愈覺得阻撓我們相愛的,其實更可能是爸爸媽媽做為父母親的自尊。我印象好深刻的是在南印臨海小城Pudukkottai遇到的詩人兼記者阿賽,他輕描淡寫地抱怨自己明明跟戀愛結婚的妻子同種姓,這段婚姻卻還是遭家人反對,「只因為我自己決定了結婚的對象,」他嘆,「說到底,父母在意的畢竟是他能不能掌握決定兒女婚事的權力呀。」
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台灣的,尤其是早期的台灣。自由戀愛在台灣也不過是這一、兩個世代才普遍起來的事啊。

印度報紙上的全版徵婚廣告。
這種「你既然選擇戀愛結婚,將來遇到什麼問題就活該自己負責」之類的論述,我在訪問其他跨種姓/跨宗教伴侶時也曾聽過好幾次。比如我們的好朋友,那個當年毅然決然隻身離開喜馬拉雅山區老家,長途跋涉到中部小鎮與不同種姓的男友相守的薩絲瓦媞,就時常感嘆:「我跟艾尼爾的婚姻好像不被允許出任何狀況。」

從Tiruvallur前往Vellore的區間火車上 。馬拉松式的訪談。

跟著朋友參加南印度的婆羅門婚禮。(Chennai, Tamil Nadu)

印度教小鎮Khilchipur。 (Rajgarh, Madhya Pradesh)

農村生活。 (Sehore, Madhya Pradesh)

朋友的婚禮。印度中部Sisodiya種姓的傳統婚俗。(Rajgarh, Madhya Pradesh)

印度女人踝上沉重的腳環是已婚的標記。

蘇西拉的哥哥蘇達卡和他的基督徒妻子夏蜜莉。兩人才新婚不久,蘇達卡就又要回杜拜工作了,我問他們分隔兩地要怎麼辦,他們緊緊牽著對方的手說:「沒關係,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愛。」
其實山迪,我倒覺得你爸媽有點像是在實行蘇西拉口中的「不合作運動」──你能想像蘇西拉已經結婚十幾年了,同住的婆婆還是堅持在日常生活中「消極抵制」她嗎?「她不會傷害你。她會照料你生活所需。我們一起吃飯、一起談笑,一切都很正常。但她就是不放棄在一些小事情上讓你感受到『你是這個家的外人』。」蘇西拉這樣解釋。而我感同身受。
「這是很多父母手中僅有的武器,」蘇西拉忍住笑,「用以展現自己的自尊。」
我還記得自己當初是在多氣憤的情況下提出這個旅行計畫的。在聽完這麼多人的故事之後,我已經不氣了,也不再懼怕了。我知道你跟我一樣有足夠的信心去迎向未來的挑戰,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愛。

山迪:我想你的時候就看這片湖。想你三兩下就穿越混亂的車潮去湖對面小店買到三秒膠,一個箭步蹲下身為我黏好突然斷掉的涼鞋夾腳繫帶(旁邊賣氣球的小販看得目瞪口呆),確認我暫時可以行走無礙後終於放心地咧嘴笑了。然後你有點不好意思地問我身上有沒有一盧比,因為你剛剛付錢時只翻找到四盧比,老闆搖搖手說沒關係但你就是過意不去。 想你的時候就看這片湖。 (Shahpura Lake, Bhopal, Madhya Pradesh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