藝術人文 用氣味與文字,穿越慾望的迷障——專訪《香鬼》調香小說家古乃方
by 李翊彤不論是寫作或調香,都是一個互動的過程。寫完《香鬼》我對畫面和幻想有一個自己的版本,但大家不要把它當成正確答案。
與古乃方相約的午後,視訊畫面上她以優雅的頭像示人,「我就不開鏡頭了,居家狀態有點狼狽。」眾人想一睹真容,她只好笑著妥協,「我開的話你們也要開。」她的言談間總能細緻地傳達感受,並不失直爽與稚氣。哪裡看得出狼狽?
在氣味與文字的世界裡,乃方創造出的每一道氣息、每一則故事如同咒語,像慾望在騷動。為了抵達內心的真實,她穿越迷障成了「巫」——對她而言,成巫無須蠱惑人心,但若停止創作,無異於失去性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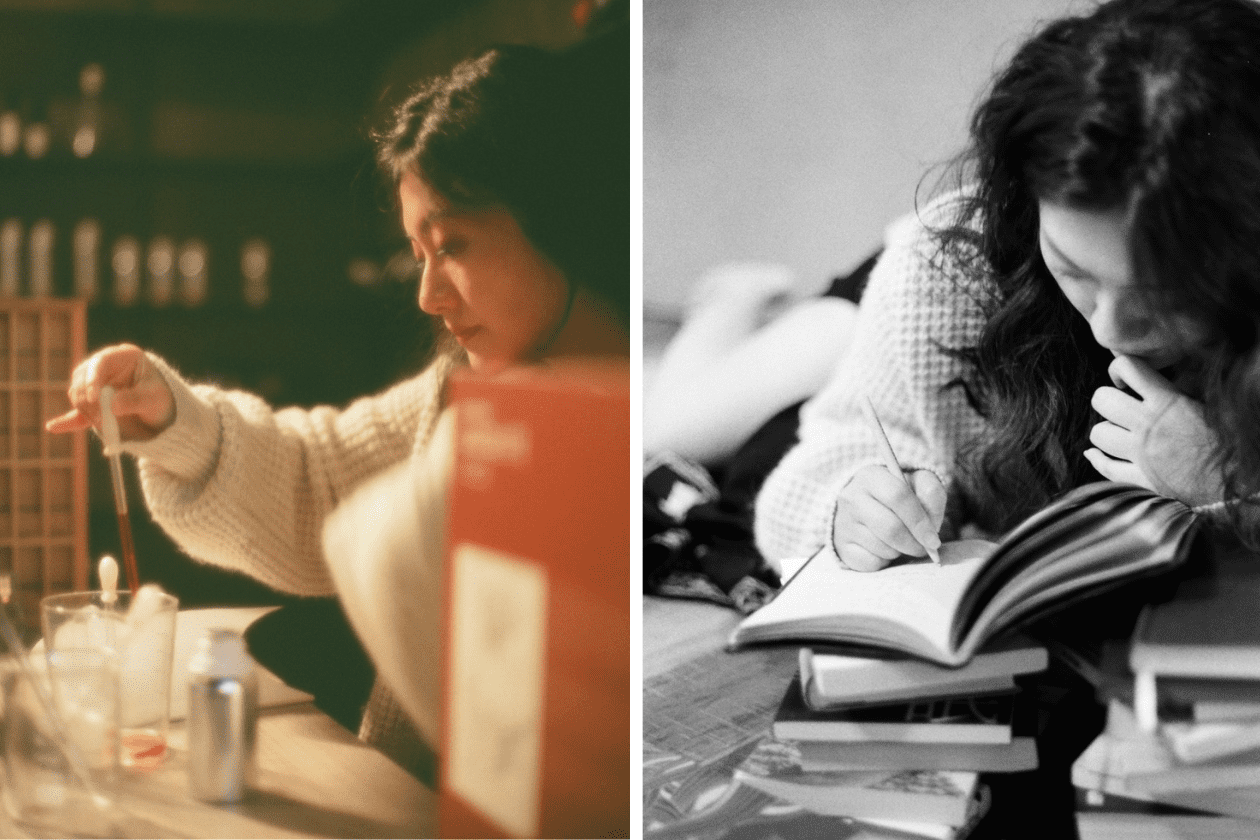
這位剛出版小說《香鬼》的調香師,總是親暱地稱客人為「香民」;日前她的調香品牌推出新作「植物野獸」、「末日花園」和「光苔」,說新也不新,因為這三款香水早在她的小說中現蹤。乃方常說:「有家才有遠方。」所謂遠方,無關追逐他處的浪漫,而是專注於內在精神的表達。如此一來,本心踏實好比香水有了瓶身、文字有了書頁,這次她跨越媒材的藩籬,想看看還能去哪。
起初只是為了泡茶:一名女巫的養成
談起調香啟蒙,古乃方回想起在愛丁堡大學讀研究所的時期,「那邊蠻有巫性的。」主修經濟顯然無礙她對神話信仰的探索,而這些讓後世得以遐想精靈、女巫和魔法的凱爾特文化,也讓身處異鄉的她開始思考,台灣的味道和英國有何不同。「下課後我會去草藥鋪買一些材料回去實驗,嘗試拼湊台灣的香氣。而所謂的草藥鋪,其實有點像我們的中藥行,只是變成歐洲版。」
儘管調香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門鄭重的技藝,但乃方並不打算受制於既有的知識框架,她認為備好紙筆、燒杯、磅秤、試管、攪拌棒,隨時都可以開始。至於觸發她實作念頭的,純粹是對家鄉味的想念,「我那時候很想喝茉莉花茶,當地的茶都蠻不合胃口的。」
乃方想著,若能取得茶葉、茉莉花的原精再好不過,這樣一來她就能調一個自己滿意的味道。但當地選擇有限,她改用癒創木,沒想到真的調出了茉莉花茶的味道;她繼續試,這次將白玉蘭葉加入其他木質材料,竟然浮現了菊花茶的香氣。「原來不需要茶,只要花和木頭就能調配出我想要的質感,就像變魔法一樣。」至此,她對這套邏輯感到著迷。

從英國取得碩士學位後,乃方在信義區擔任金融交易員。市中心的人們穿梭於水泥叢林、標配套裝和皮鞋,她是其中一員;然而,緊挨著光鮮亮麗的另一側,當時租屋處所在的吳興街屬於較老舊的街區。「每次下班經過騎樓,都很怕有蟑螂老鼠突然掉下來。一回到家,我會把托特包放在地上盯著看,看著看著,直到包包伸出兩隻觸角⋯⋯」
白天畫全妝,夜裡打蟑螂,凌晨再爬起來看聯準會升息,生活毫無品質可言。「那時候常常睡不好,香變成撫平我焦慮的媒介。」夾縫中求生,乃方不忘擴充對調香的理解,也不曾丟失原有的寫作興趣,「後來我也做過政府智庫的經濟研究員,閒暇時每天寫1000字,〈塵埃〉是我人生中寫的第一篇小說。」她把吳興街當作線索埋入筆下的世界,同時意識到——自己其實處在一個能施展魔法的場域。
「那裡像是城市的皺褶,又像是女巫居所的邊界。」而她,正是那名沉潛其中的女巫。
調製有律動的香水,醞釀最精緻的脾氣
那段上班族的經歷不能說沒有收穫,至少乃方發現自己不適合與人共事,「我喜歡獨立完成所有事情,調香和寫作剛好都可以。」笑稱性格頑劣、不願被體制歸化的她,抓準機會就要逃。她觀察彼時台灣香水市場上的「創作香」不多,決定辭職後大膽成立氣味品牌「方方(Eau de parFang)」,不滿足於表面的芳香,她更重視香調之間的層次,她要特別。
10克玫瑰、10克菸草會有什麼樣的火花?「色彩學習作」是品牌成立後推出的第一個系列,延續了年少時學畫的經驗,乃方將色彩學的邏輯套用於調香的尺度,使香材間的互動時而協調均衡,偶有支配和隱沒。玫瑰與菸草也不再只是單調地添入,而能:玫瑰1滴、煙草1滴,玫瑰1滴、煙草1滴⋯⋯,這就是香的律動。

「『聯覺』在我的腦袋或靈魂裡可能是有通的。」當感知沒了壁壘,她縱橫五感以拓展氣味的可能,亦循著氣味去打磨文字的疆域。2020年,一直有寫作習慣的她把作品集結成短篇小說《塵埃》,她希望香民穿了方方的香水,也能認識她的字。
對許多人來說,每天泡在香氣和文字是求之不得的浪漫。然而主理一人工作室並不酷炫神秘,得自己包貨寫文案,回覆訊息的身段更要柔軟,「我會假裝自己是小幫手Gina、Tina,甚至是Andy之類的——標籤掉了是嗎?馬上補一個給您哦。」像人格分裂。
收過客人抱怨香水香到睡不著,但這不是最荒唐的,「也有客人來找我調香水,說要一種20年前跟妹仔抽過的維珍妮涼菸,薄荷味的。」這位寂寞的男人約晚上11點面交,騎著擋車來,還得寸進尺載著她去深夜咖啡廳。當下不知道怎麼婉拒,如今回想倒成了一件令人發笑的奇遇。
成巫之道不像一條通往避世的路徑,但或許乃方要的從來不是遁逃,而是抵達自由。「現在我會請香民在訂單備註最喜歡的三種香材,或是給我一個畫面、一首喜歡的歌,但不保證一定用到。」懂得設立界線,她的原則張弛有度,一如幾年前的小說作品《塵埃》摺口的作者介紹:「forte forte,這是我最精緻的脾氣。」穿梭於五感的律動,一記強音記號定調了乃方創作的濃厚情感。
此刻,她既是調香藝術家,也是小說家,有香民與讀者懂她。
調香與寫作,不一定求真
回顧《塵埃》,乃方對當時的青澀感到羞赧。但正是那股青澀,埋下她最早的困惑:如何轉化生命中難馴的氣味?帶著疑問,她開啟了《香鬼》的創作,先完成了〈植物野獸〉和〈龍血〉兩篇,進度卻卡住。「一直不知道這本書該長什麼樣子,剛好小說有拿到國藝會的補助,我就把錢拿去諮商了。」為期一年半的時間裡,乃方來回進出諮商室6、70次,她渴望得到解法,但諮商僅是一面鏡,映照出來的也只能是自身。她明白小說若要繼續,那帖藥得自行煉製。

《香鬼》講述了調香師北北在各種關係中的周旋與療癒。這趟旅程走得蹣跚,開篇是她與紅毛猩猩安在調香過程的扶持和較勁,之後她在諮商室和康老師交鋒、與科技新城的陽剛工人進入婚姻,並遇見了萃香師香鬼。
小說中的萃香師求真,採集總是不惜手段;但對故事或現實裡的調香師而言,特定香材的取得不是必須,她們往往只是依憑氣味的記憶,盡可能貼近自己所認知的真實罷了。價值體系的衝撞帶來痛苦,乃方旁觀北北的傷,有時也煎熬,「北北這個角色是我的一部分,我讓她長出自己的生命,去反省為什麼做這些事。那時候我會覺得格外痛苦,因為我可能不是這樣的人。」她既是北北,也不是北北。
那麼,對她而言什麼是真?「我覺得不論是寫作或調香,都是一個互動的過程。寫完《香鬼》我對畫面和幻想有一個自己的版本,但大家不要把它當成正確答案。」創作是自身與作品的互動,也是作者與外界的互動;香水不一定求真,書寫亦然。
真真假假,所謂陰陽香臭和新舊,只是相對,都是比例的調配。於是乃方寫出一隻有調香天賦的獸——而今又有誰記得1980年代的台灣,曾有一段走私紅毛猩猩當寵物的歷史——也寫貓空後山的大麻田、暗潮洶湧的諮商空間⋯⋯她擷取那些不盡然存於自身、也不見得代表眾人尋常記憶的「真實」,把人臉模糊、將地點移植,情緒像香材,有賴精心配置,而她用筆墨記下。
眼下的一切,都是性感的力量
五月底《香鬼》的書稿完成後,乃方去了一趟芬蘭駐村,見識到真正的無盡夏日。駐村期間由單位保管藝術家們的手機,少了干擾,她形容自己身在奇點——一個數學概念中,因為趨向無限而無法定義的狀態。她的肉身恆在、感官敞開,卻平靜無求。「未來彷彿是無限當下的延伸,我完全在『在』裡面,那是沒有時間感的,也無法調香。」
何時才能從奇點下降?乃方說是意識到「我」的時刻。
「那時有個日本藝術家照片拍得超好,我就問她可不可以幫我拍,但她不要,跑去找住我隔壁的另一個金髮女生當模特。我心裡就覺得很嫉妒,為什麼選她不選我。」嫉妒感是一種自我作祟,一旦察覺,靜止的時間也開始流動。「從奇點下降後,就不只是『在』了,還會產生想做點事情的慾望。但,我也提醒自己曾經走入奇點裡,要記得帶著意識被撐開、寧靜寬敞的品質去創作。」
駐村行程結束後,乃方一返台便奔忙於新書的發表。面對群眾,她聊《香鬼》如何幾經修改、反覆折磨;也聊芬蘭經驗如何影響「森林妖魔」和「水底妖魔」兩款香水的調製,前者記下了浴間桑拿和樺木葉的拍打,後者則是藉玫瑰將海藻的鹹腥轉化。「樺木的味道是很原始的燃燒感,但聞完其實不可怕。」她接著說:「我還會拿一盒煮好的豬油,在上面鋪滿玫瑰花瓣,每天換花,直到豬油凝脂充滿花香。」她說,眼下的一切,全都是性感的力量。


有人問:未來還會不會有關於調香師的作品?乃方請大家先不用擔心,經營品牌的香水文案還是得寫,此刻手邊除了散文集,還打算寫女馴鷹人的小說,當中肯定少不了氣味描寫——但真要說調香師的故事,可能還真的沒有了。
「寫長篇小說,其實是帶著困惑寫的,能不能走到終點多少心存僥倖。《香鬼》因為有北北的困惑,才撐起這麼大的空間,所以困惑是我的動力。」只見她不疾不徐,坦然地說:「但我目前的調香生涯,已經沒有新的困惑了。」
同場加映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