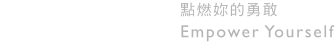女力 We wanna be 我不是不孝,只是在學怎麼重新當女兒——專訪《長女病》作者張慧慈
by 陳品嘉長女病的好轉,從來不只是個人的療癒,而是關乎整個家庭與社會對責任分配的想像。
早上九點,張慧慈準時出現在約定的咖啡廳。她鐵口直斷,說願意配合這麼早工作的,多半是長女。她說中了,在場兩位編輯恰好都是長女。
並非神機妙算,1988年出生的她當了三十餘年長女。出身藍領家庭,苦讀進入台大社會研究所,用社會學視角關注階級與性別議題。今年出版《長女病》,她把目光投向自己與不同世代的長女,寫下她們的故事。

這本書召喚出藏在家庭、社會、職場默默扛責的身影,他們不一定是長女,卻都有「長女體質」,習慣將責任攬在身上,經常是成全弟妹的犧牲打,父母長照第一選擇。常有讀者私訊或在分享會發出隱忍多年的求救訊號:我很痛苦,怎麼辦?
這些讀者的生命經驗,也讓「長女們」的輪廓更加清晰。張慧慈印象很深刻,有弟弟送這本書給姊姊,希望她不要再活得這麼辛苦;還有6、70歲的讀者分享,她終於明白兒子為何堅持要她來參加《長女病》分享會,「因為他希望我從長女的責任走出來。」
長女是如何養成的
張慧慈自己,就是久病而成的良醫。她的解方不是拍拍抱抱,也不空談轉念正能量,而是一路上運用社會學與心理學覺察自我的經驗。
「長女病」書名源自於年輕世代語言,十分貼切,這種「病」不是偶然,而是傳承了母親身為長女的生命模式。張慧慈的父親瀟灑自我、置身事外,弟弟罹患腎臟病,高額醫療費全落在母親肩上。母親不眠不休工作養大四個孩子,還得照顧年邁的公公。從小學起,張慧慈就是母親的左右手,努力做弟妹的榜樣。

幾年前母親身體出狀況,她默默預先認領所有照護責任。「那時發現如果我媽走了,我好像活著就沒有意義了。我最大的問題,就是一生想要榮耀我媽,希望她被稱讚『妳好會教小孩』。」
透過心理諮商,張慧慈釐清盤根錯節的內在傷痕,但也意識到要真正理解「長女病」,還需要不同視角的介入。她解釋,心理諮商常從童年經驗梳理原生家庭創傷,對自我療癒確實有幫助。「如果只是用個人視角來看待長女病,有時反而會懷疑:是不是我比較苦命?為什麼這麼衰?」
張慧慈觀察到許多女性朋友到了某個階段,為了照顧需頻繁看醫生的年邁父母而辭職或換工作,她也常被親戚耳提面命:「以後爸媽老了,妳要回來顧。」
「我開始思考,也許不是原生家庭的問題,而是整個社會預設長女就該扛起所有責任。」
從「承擔」走向「鬆動」
求學期間拚獎學金貼補家用,卻換來母親一句:「我又沒有叫妳這樣做。」在諮商心理師引導下,張慧慈開始練習:媽媽沒開口,就不要主動提供協助。
起初妹妹接手照顧母親,但有些反彈,覺得姊姊太過分。直到有天接到保險業務來電,才發現母親積欠十萬元保費未繳,再不處理保險就要失效,妹妹只好硬著頭皮向朋友借錢補上。更讓姊妹生氣的是,這已經不是母親第一次拖欠保費。
這一刻,妹妹首次意識到張慧慈背負了多少責任,她主動提出:「我們要一起改變媽媽,否則整個家都會垮。」

長女病的好轉,從來不只是個人的療癒,而是關乎整個家庭與社會對責任分配的想像。「分工」是她提出的解方。
不過,對長女來說,要求手足分工就像發動一場千夫所指的革命。當張慧慈從社會學視野重新審視自己背負的不公平,才找到切入點建立新信念:我不是卸責或不孝,而是要鬆動傳統社會結構。
張慧慈面露懺悔,坦言自己也曾對朋友的女兒脫口而出「哇姐姐好懂事喔」。長女病,不只是一個人的內傷,而是幾代人累積多年的慢性發炎。要治好,快不了,不輕鬆,可能還需要很痛的代價。
那些起身揭竿的長女,有的被弟妹罵自私,有的被父母指責愛計較,甚至與家庭決裂。但最讓張慧慈驚訝的是,她們還是堅持住了,只因為「我不想再跟自己過不去」。

張慧慈最「過不去」的人,曾經是父親。
小時候差點被父親賣給私娼寮,她成績好卻被嫌棄「不如長得好看快點嫁人」,言語攻擊持續到她長大成人仍未停止。
求學時,她試圖用理論梳理與父親的關係,卻得不到答案。社會學說不清的、心理學摸不透的,十年後才發現因果早就寫在紫微斗數命宮裡:從她的命盤來看,父親就是「會用言語傷害她的人」;而對於兩個妹妹,一個「像朋友」、一個則「無關緊要」;但到了弟弟命盤,父親竟成為「最大貴人」。
這個發現讓她釋懷許多,她學習命理兩年了悟的,是不應違逆本性去活。父女緣淺天註定,不勉強親近也不逃避,玄學讓她不再奢望父慈女孝,認命當對方的凶星,開戰就當能量釋放,原本撕裂的父女關係,反而稍微鬆動了。

當女兒,也需要練習
張慧慈發表過文章〈愛自己,就是把自己當女兒養〉,但慣性犧牲自我、長期浸泡在「我不配」情緒裡的人,如何敢將自己放在手掌心?
「你去看幸福的家庭怎麼對待女兒,或者模仿身邊的次女。」長女的課題從家庭延伸到職場。升遷之路頗順利的妹妹,有次對她傳授職場鐵則:「我會做事,但不做自己看不下去的事。」警世金句猶如當頭棒喝。張慧慈說,曾有工作任勞任怨的讀者,聽從建議模仿次女同事有所不為的工作態度,能力反而更被老闆珍惜。
那麼,要如何珍惜自己?張慧慈「養自己」的方式都很生活,很細節。她和長女朋友的新練習,是「不點最便宜的餐」。過去先看價格、而非依喜好點餐,是為了體恤爸媽,再不然就是點「弟妹第二想吃」的餐。

這些微小習慣,都是長年練就的察言觀色與習慣性犧牲。如今她決定要點想吃的,蔬菜蛋白質豐富的,重新給自己選擇權。
聽起來很率性、很做自己,但不可能一次到位。「立刻徹底改變太困難了,先從模仿開始會容易些。透過模仿,你可能會發現有些不太習慣,那就是你正在慢慢長出新的樣子。」
練習重新養自己的過程中,她想起兒時某次被同學欺負,與老師溝通未果,母親直接殺到學校討公道。張慧慈語氣緩了下來,「必要時反擊不尊重你的人,是對女兒最好的教養方式。」
原來,母親不是不愛她,只是被現實壓逼幾乎滅頂,長女是浮木也同時是戰友。兩代女人要共同撐持一個家,太早負重,她幾乎忘記,弟妹出生之前自己也曾是獨享寵愛的獨生女。
年過三十重新養好自己,也讓母女再回到原位。所謂和解,不過是我好好當女兒,妳好好當媽媽。

長女限定的快樂
今年四月張慧慈接受《鏡週刊》採訪,記者問她如果重新投胎想當誰?她覺得人生好累,最想當無憂無慮的小妹。
但當聊起近期計畫,她早有一長串待辦事項:舉辦匿名線上分享會「長女聊天室」,籌備實體活動,一起覺察慣性重新養自己。還要與出版社推出講座,分享從社會學切入寫作,幫助創作者找到新的書寫視角。
不只如此,她連攻讀博士學位、職涯規劃都完整擘畫出來,忠實體現「嘴上喊累,身體很誠實地規劃五六七八件事」的長女體質。
距離週刊採訪不到三個月,她的心境出現大轉折。出書後與家人的互動、讀者的回饋,讓她看見長女特質的好:善於觀察、風險控管能力佳、強烈的學習欲望......「我們超多優點好嗎?」笑容中,有一分捨我其誰的自信。
當姊姊,也比想像中快樂。「我很早就看見社會運作的方式,長女會成為視野入口,引導整個家庭看待事物的方向和價值觀。」例如她讓媽媽了解並接納同婚的意義,甚至不愛看書的妹妹也開始從社會學找答案,還鼓勵小妹多讀書。

了解各世代長女的處境,成為張慧慈的興趣。她分析說,母親那一代的長女通常會被要求賺錢供弟妹唸書,甚至婚後還要持續資助娘家。到了她這一代,往往要當弟妹的榜樣,同時承擔更複雜的雙重挑戰:一方面要療癒自己,一方面要抵抗原生家庭的舊模式,避免把這套不公平的腳本傳承給下一代。
即使現代經濟相對富裕又少子化,讓長女獲得更多資源,但張慧慈觀察到,如今仍有不少父母規劃晚年時,預設由女兒照護,若只有兒子則傾向入住養老院。「可能青春期還感覺不到,但到了父母需要長照時,『長女病』就會真正浮現。」
革命尚未成功,長女仍須努力。但翻轉舊觀念的路上,不能拋棄照顧自己的餘裕。
訪談結束,張慧慈趕著赴下一個約。原以為是工作,她說,是要去做臉啦。隨即補充,「這家工作室有開發票報稅喔,很棒吧,就一直給她做……」
保養皮膚也要顧及制度與正義,這一點,實在非常張慧慈。